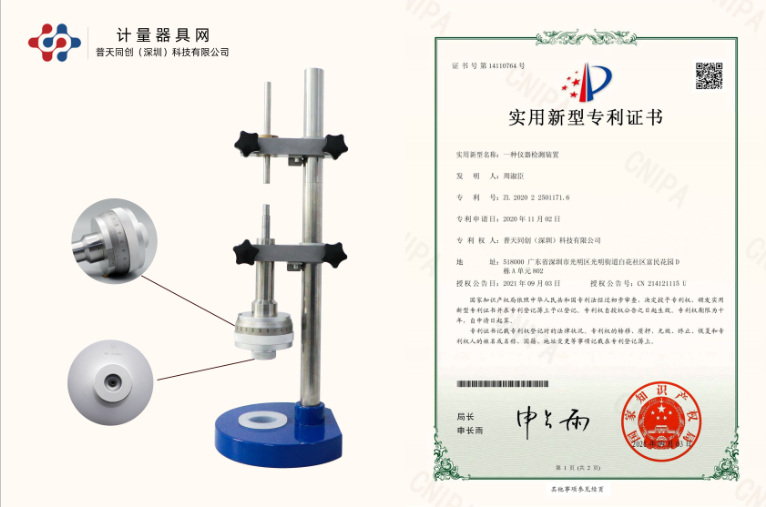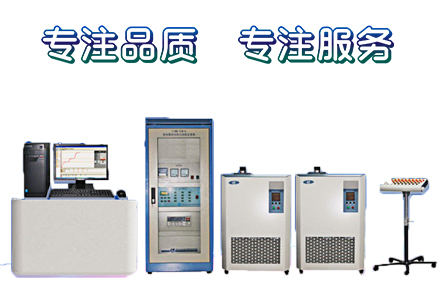我總覺得,如果我們都能像說相聲的一樣去面對生活,這個世界也許將會變得更加美好。
生活總會有苦難,黑暗的心情會在任何情況下不期而至,你隨時可能會為莫名其妙的煩惱暴躁,而且無論如何擺脫不開,就像身處夢魘之中,明明知道它將離去,但是覺得總要等上幾千幾萬年—這也就是佛家所謂的“無名”。
這種時候,就很需要像相聲一樣面對生活,那是這樣一種心態:不否定一切卻調笑一切,不侮辱一切卻曲解一切,不像英雄似的直面困難卻用近乎輕浮的方法解決困難,讓自己開心,讓自己永遠立于不敗之地。
有點阿Q,絕不犬儒。

相聲藝人可能是最喜歡用這種方式生活的人,因為這門藝術已經在他們身上烙下了深深的痕跡,并以他們為載體一代代傳承下去。
舉一個我自己的例子。這次的例子是臺上的“現掛”。“現掛”就是根據現場的情況即興編的詞,在有些情況下,現掛的目的是解決現場發生的問題,把觀眾的精神重新集中到舞臺上來,比如侯寶林先生那個著名的“救火車”的例子。說《婚姻與迷信》正說到“新娘子邁火盆,這多危險,要引起火災來怎么辦?”忽然外邊救火車聲音大作,觀眾都往外看,這時候觀眾的神已經散了,再往后說什么都不樂了,侯先生不慌不忙地說:“你聽,這不定是哪家又結婚呢。”一個山崩地裂的大包袱之后,觀眾的精神又全都回到了臺上。
這只是現掛的作用之一,還有些現掛是說給演員自己和后臺人聽的,功能性不強,但在演員自己聽來,無比可樂。
我是睡不醒的那種人,平時只要是自然醒,都是十個小時以上。某才女說:你只在睡覺這件事上有天賦。
有一天下午演出,差點睡過了。頭天晚上熬夜到四點多才睡。早晨十點多鬧鐘響了,一想再睡個回籠覺吧,剛十點多,也晚不了。誰想到再一睜眼就快三點了,而下午的節目是倒數第三,三點二十就得上了。嚇得我趕緊起床,打車去園子。進園子后臺,已經快三點十五了,穿上大褂,基本上就接場了。周圍人都向我怒目而視,臨上場前一分鐘我跟王文林先生說了說起晚了的事,就算向大家道過歉了。
節目中,我讓我的主角加了兩句話,說:“我早晨十二點多一起床,一看春光明媚??”王先生攔著:“不對啊,十二點多怎么還早晨啊?”我說:“十二點多不算晚,我們說相聲的都得晚睡,十二點起不新鮮,我們還有三點才起的呢。”
連王先生帶我都繃不住樂了,我還聽到幕后邊傳來大笑之聲。
這也算是自我挖苦,算另一種形式的道歉吧。
再舉一個比較終極的例子。在這個例子里,相聲藝人作為“江湖人”的本質暴露無遺。
說相聲的以不吃眼前虧為原則,逮著什么就說什么,得機會就罵罵別人,沒有機會就罵罵自己。在說相聲的嘴里,上至帝王將相,下至販夫走卒,外至親朋好友,內至爺娘妻子,無一不說,無一不開玩笑,甚至是無一不糟蹋,可稱是百無禁忌。
曾經有一個相聲老藝人與人口角,被人指著鼻子罵道:“我×你媽!”明顯,對方已經到了氣頭兒上,只要是他一還言,必要挨打,可是話擠對到那兒,不還言又實在說不過去。只見這個相聲老藝人聳聳肩,不屑地扔下一句:“誰出來演出還帶著媽呀?”擠出人群揚長而去。
圍觀眾人無不暗挑大指:這可算得上是毫無原則地趨利避害的典范了。